中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迅速,但煤电与可再生能源绑定发展的模式拉动了额外的煤电投资,这为减排带来挑战。
▲哈密石城子光伏电站。政府规划建设大量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分布在人口密度低、电力需求有限的西部偏远地区(比如戈壁、沙漠),统称为新能源基地。图片来源:Zhao Ge / Alamy
过去的10-15年,中国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的节奏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从2005年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以固定优惠电价鼓励风电光伏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历年的风光新增装机量占世界总量的50%甚至更多。201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风电年增长20到35吉瓦;而光伏后来居上,增长更快,在30到50吉瓦。二者合计,在2015年后的5年,大体年增长50到60吉瓦。
2020年开始的三年,尽管有疫情影响,但是风电光伏的装机保持了韧性,大幅增加到每年100吉瓦以上。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进一步提速的一年。国家能源局在2023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全年新增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等)超过150吉瓦,其中风光合计125吉瓦;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3%,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能源局发布会报告的测算结果认为:“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简单推算,这相当于1千瓦可再生电量,实现837克二氧化碳的减排。这一度量基准对应于一个度电煤耗300克标煤煤电厂的排放水平。
我们认为,这一减排效果相比实际情况存在高估,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特色“新能源基地”的特定并网安排带来的运行与投资影响。
可再生能源与煤电“齐头并进”
可再生能源进入电力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替代传统能源发电,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是个学术、政策与工业界的热门话题。机组的减排效果会因为电力系统特点不同而有所区别。也就是一个新的零排放的风光电源进入系统,到底会挤出何种其他电源的问题。
成本最小化的电力系统往往实行经济调度,即机组按照成本从低到高的调度排序来满足变动的电力需求。可再生能源进入发电序列,将挤出高成本的边际机组,实现对应机组排放强度的减排效果。因此,如果边际机组是水电(比如北欧地区),那么减排几乎是零;如果是依靠昂贵的天然气发电(比如2022年天然气价格暴涨的西欧大部分地区),减排对应天然气发电的排放强度(根据效率不同,大致在400-600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如果边际机组是煤电(比如煤电占据50%以上份额的印度与中国),那么单位发电量将减排700-1000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以上是基于100%替代煤电的测算,即理想状况下的最大减排效果。
编者注:什么是经济调度?
经济调度是一种对可用发电资源进行排序的方法。序列中边际成本最低的发电机组(比如可再生能源)最先上线以满足需求,而边际成本最高的发电机组(比如煤电)最后上线。以这种称为经济调度的方式调度发电,可以最小化短期电力生产成本。
在中国,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新装机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是为了并入本地电网来建设的,与传统电源不构成替代关系。政府规划建设大量风能和太阳能容量,分布在人口、经济和电力需求有限的西部偏远地区(比如戈壁、沙漠),称为 “新能源基地”。与新的或现有煤电捆绑,电力通过特高压输电专项工程传输到东部沿海地区。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规定,在“水电、风电、光伏、煤电”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份额“不低50%”。考虑到水电外送是100%的可再生能源,测硫仪,因此即使煤电含量达到70%仍满足上述总体约束。因为这种“配套”,可再生的投资,引发了煤电的进一步扩张(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风光,也不会引发对应的煤电建设与投入运行)。二者甚至是互补的关系。已建成线路的运行记录(2021年,2020年,2019年)也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线路的跨区输电量中,风电与光伏的电量比例20%-40%。最新计划中的新疆哈密——重庆输电专线项目,配套可再生1000万千瓦,煤电400-600万千瓦。
西部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可以减少东部地区的煤电装机吗?答案是:大致不会。电力系统存在N-1原则作为基本安全要求。它指的是:电力系统任何单一设备故障,都不应该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东部地区必须在假设整个线路断掉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身供需平衡。考虑到煤电机组的寿命35-40年,而风电光伏普遍在20年左右,这种对煤电投资的拉动造成的长期排放锁定风险就更大了。
从运行角度,可再生电力替代燃煤发电,也强烈区别于电量1:1直接替代。西部地区70%的煤电,加上30%的风光发电,替代东部电力需求旺盛地区的边际机组(所谓:满足需求的成本最高的机组),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煤换煤”。即使受电地区边际机组比西部新建机组效率更低,从而具有更高的排放强度,这一替代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也会因为各种因素大大折扣。比如:显著长距离输电线损;东部地区调峰深度增加,从而效率变差;本地汇集上网的线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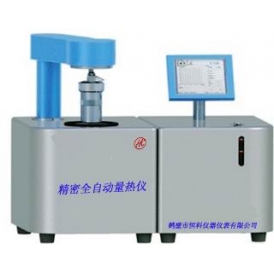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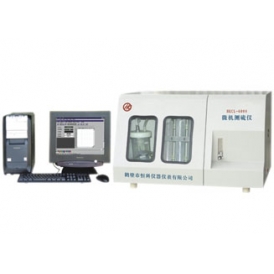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  客服2
客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