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带,同时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资源富集区、原煤生产加工区和煤炭产品转换区,40%以上的流域面积蕴藏煤炭资源,被誉为“能源流域”。该流域有12个探明储量超过100亿吨的大煤田,包括宁东、陕北、神东、晋北、晋中、晋东、黄陇、河南、鲁西九大国家大型煤炭基地;查明煤炭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的45%,原煤产量约占全国的60%。黄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在相当长时期内既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也促进了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重点产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黄河流域主要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炭资源开发集中区域大部分处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加之煤炭资源开发产生采煤沉陷、耕地损毁、水资源和地表生态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传统单一式、被动式的“末端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有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要求。
因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可为客观认识黄河流域煤炭矿区日趋严峻的产业、生态、环境问题,变革煤炭矿区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功能,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同时还可以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更好地将建设美丽中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方案。
煤炭产业生态化
前提是辨识开采全过程的环境影响
产业生态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第一层次。环境容量是具有强制约束性的煤基能源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以往认为煤炭资源开发破坏环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的关系。而根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可以做到生态化,即在开发煤炭的同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
也就是说,测硫仪,煤炭产业生态化是促使产业经济活动从有害于生态环境向无害于甚至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过程转变。作为资源开采型产业,煤炭开发、建设与生产过程给矿区生态环境带来人为扰动与生态破坏。煤炭、覆盖层、水系、地面植被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采煤扰动了这个生命共同体,因此,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应覆盖煤炭开发全过程,包括资源勘探、矿井建设、煤炭开采、退出闭坑、生态恢复及深加工利用等方面,通过主动保护、修复甚至重构生态体系,使煤炭开发更有价值。
在行动上,依靠科学技术手段,辨识煤炭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扰动规律,明确生态-水-植被-土壤-煤系地层破坏特征及关键路径。基于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理念,应协同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环境承载能力与煤炭开发产业链的生态环境保护,即开采前进行精细化地质勘探,开采过程中进行精准化减损,开采后进行精确化恢复利用。通过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如保水开采、建设“海绵矿井”)、污染综合治理(如建设“无废矿井”“无废矿区”)、生态修复等手段,建立开采过程中同步、同时的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模式。通过妥善处理矿产资源、水资源、地表生态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建成绿色矿山,打造生态矿区,实现“采煤不见煤、排矸不见矸、污水不外排、风起不扬尘、车过不起灰”。
为此,应统筹推进产业生态化,精准区分煤炭开发的生态损害,变被动治理为主动引导,推动煤炭产业实现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治理”,从“先开采后治理”走向“边开采边治理”,从“先开发后保护”走向“开发协同保护”,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系统综合协同治理的方案,构建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生态保护模式。
生态产业化
要求“绿水青山”可计量、考核、获得
生态产业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第二层次。在产业开发协同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以生态开发促进产业多元发展,既强调生产活动的绿色低碳转型,又强调生态环境的价值转化。生态产业化不仅要严守生态红线,而且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挖掘、开发、创造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产业体系建设,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也就是说,生态产业化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资产化、产业化,另一方面是让“绿水青山”转变为可计量、考核、获得的“金山银山”。不仅要考察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要考察其生态价值。同时,生态服务、生态产品、生态碳汇也是经济资源,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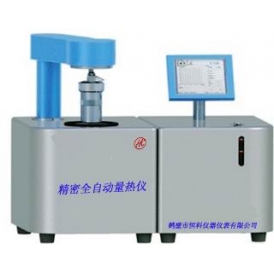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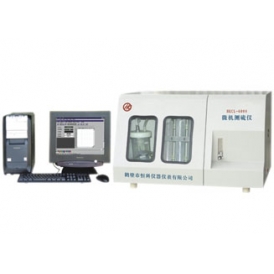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  客服2
客服2